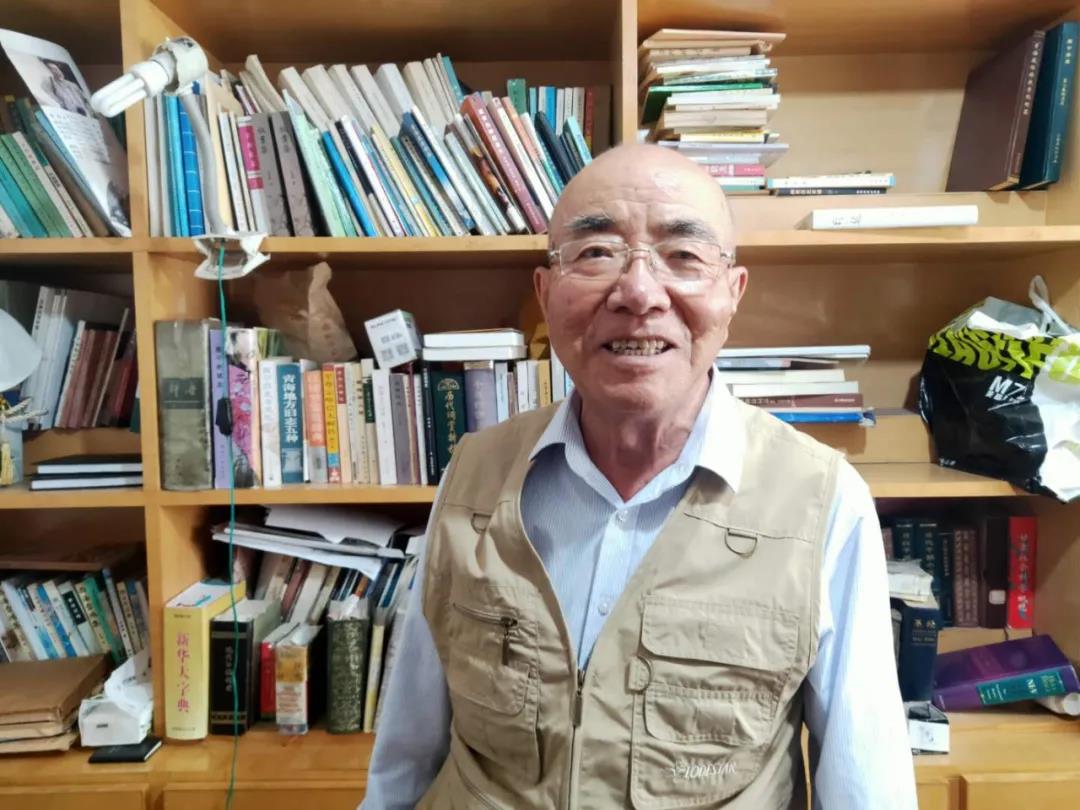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互换思想的工具。西方传说中,早期人类不分族群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语言的统一让人们拥有了强大的力量,人们甚至建造起了一座直通天界的宝塔。人类的力量让上天恐惧,上天不仅摧毁了宝塔,还让人类的语言变得“四分五裂”。从此,人类的语言分为了很多个语种,不同的语种又分化出诸多方言。
古老的传说即说明语言的伟大,同时也反映了人类语言的繁杂。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隅的青海,历来是文明交流与民族交融的大通道。历史上,不同族群在青海长驻短栖,不同文明在青海相互碰撞交融,从而形成了青海文化多元、民族众多的人文风貌。这种风貌也体现在了青海方言中。青海方言,从远古走来,带着鲜明的时光烙印,青海方言兼容并蓄,闪烁着文化融合的流光溢彩。青海的方言寄托着高原人的情感,也凝聚着历史的沧桑。
开讲人 朱世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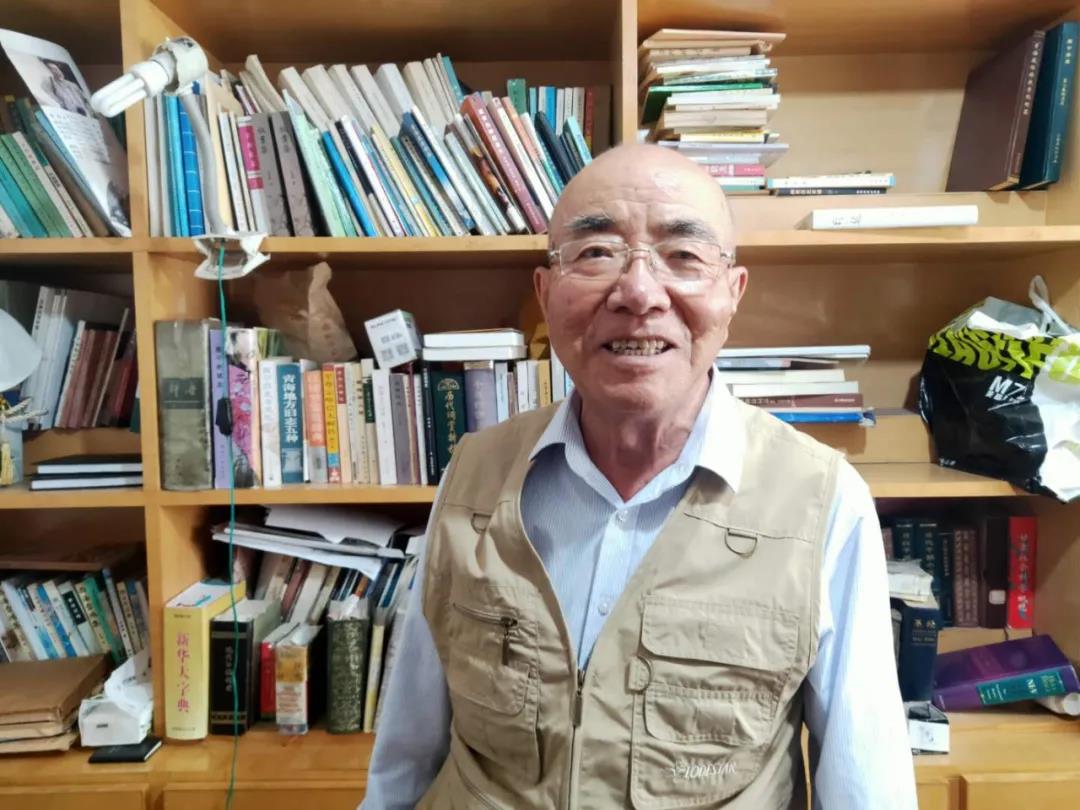
青海方言 记忆乡愁
青海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北方方言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方言,也称官话。一个方言区分为若干个方言片,称为次方言。方言片还可以再分为方言小片。青海汉语方言主要流行于青海的农业地区以及农牧交会区,根据发音特点大致可以分为数个方言小片。青海方言包括以西宁、互助、平安、大通、湟中等地为主的西宁方言区;以循化、化隆等地为主的河州方言区;以民和为主的民和方言区以及以乐都为主的乐都方言区等。这几个方言小片区的方言有所区别,但百姓之间可以彼此听懂,互相交流。青海汉语方言形成于何时,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但语言学家普遍认为,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青海的人口迁移关系密切。青海古属羌戎之地。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随着赵充国屯田河湟,大量汉族军民进入河湟地区。据赵充国上奏于汉宣帝的《屯田十二疏》中记载,当时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吏士万人留屯”河湟,随着中原汉族移居青海,汉语也传入了青海。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河湟地区各民族迁徙杂居。鲜卑秃发氏、吐谷浑以及拓跋氏都曾经略河湟。隋唐时期,河湟地区基本处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湟。史书记载,唐穆宗时期,刘元鼎出使吐蕃,在今天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鄯镇遇到几位老人,他们哭着问刘元鼎“天子安否?”说明当时河湟地区虽被吐蕃统治,但依然有很多汉族百姓在此生活。唐代诗人司空图写过这样一首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在当时,语言的交流超越了政治割据和战争的纷扰。宋初,唃厮啰在河湟地区建立了青唐政权。唃厮啰政权虽为吐蕃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李远所著的《青唐录》是记载唃厮啰统治西宁时最权威的资料,书中记载,当时青唐城流行的交际用语还会汉语。到了明朝,无论正史还是传说都有大规模的汉族百姓移民青海戍边屯田的记载。不仅在古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发展西部的需要,自全国各地的人移居青海。形成了又一次的青海移民潮。回顾历史,两千多年来,不断迁入青的汉人带来了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与世居民族语言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青海方言。

青海汉语方言是一种非常古雅的语言,它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青海地处我国内陆,因为交通不便,处于一个闭塞的环境当中,这使得一些古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得以保留。据考证,青海汉语方言中最古老的古汉语可能是“纣”。青海人习惯骂脾气别扭、做事违背常理的人为“纣式”。纣是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的谥号。史书记载,帝辛生前残暴无道,因此被称为纣王。纣是一个贬义词,“纣式”刚开始的意思是像纣一样残暴的人。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这个词汇的意思逐渐泛化,语义也比以前轻微了许多。还有青海人问怎么样,怎么了?习惯说“阿门?”“阿门”也是一个古汉语。《敦煌杂录》也写作“阿莽”,意思也是“怎么了”。“德薄”出自《周易》,意思是德行浅薄。在青海,这个古汉语词汇一般用在形容人家道中落或是遇到倒霉事的时候。意思是这个人之所以会家道中落或者遇到倒霉事儿,是因为积德太少。青海方言中的“央及”也是一个古汉语词汇。它最早出现于元代关汉卿所著的《救风尘》中。书中“央及”的意思,与青海方言中“央及”的意思基本相同,就是恳求、拜托的意思。青海人形容一个孩子不上进会说:这个娃娃不胎孩(音译)。“胎孩”源自金代董解元所著的《西厢记诸宫调》。有些流行于青海汉语方言中的词汇,不仅保留了古义,还保留了古音,如“滑”。有语言学专家考证,滑的古音读gū,滑稽古音读gū jī,意思是言行引人发笑。《汉书》记载:“东方朔为滑稽之雄”。至今,青海方言中仍使用“滑”的古音和古义。青海话说“这个人说话滑(gū)啊!”意思就是这个人说话非常有趣。像这样的古汉语词汇,在青海汉语方言中还有很多。例如:尪羸,形容人瘦弱、病情沉重。寻趁,意为别人不理你,你还自己找过去套近乎。先后,《汉书》中有记载,意为妯娌。叵烦,形容非常烦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古汉语词汇是在什么时候融入到青海方言中的,目前还没有定论。也许是从汉代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后,流传下来的词汇和语法,也有可能是明朝洪武大移民的过程中流传到青海,融入到了青海汉语方言中。
在青海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据说青海的汉族有很大一部分是明朝时从南京珠玑巷(也称朱子巷、竹子巷等)移民而来。事情的起因是明朝洪武年间的一个正月十五,南京珠玑巷的民众在庆祝时,制作了一个大脚马猴的滚灯(也有说是扎了一个大脚马猴),有人认为这是侮辱了朱元璋的大脚马皇后,于是,朱元璋一怒之下,就将珠玑巷的百姓发配到了青海。传说的真假现在已无从考据,但是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年间,政府的确组织过大量原本生活在江南、中原等地的百姓移民西南和西北。江南百姓的到来,也把吴侬软语带到了青海,最终融入到了青海汉语方言中。吴侬软语也就是吴方言,主要流行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吴侬软语的加入让青海方言听起来更加柔美,语义也更加丰富。在北方方言体系中,都称爸爸的姐妹为姑姑,青海汉语方言却称为“孃孃”,这个称谓与南京人对姑姑的称谓是一样的。还有很多青海人称妈妈为“姆妈”,称爷爷为”阿爷”,这些都与南方方言相似或相同。青海不产大米,但是在很多青海汉族百姓家中,都有一件叫“米柜”的家具。米柜是一个100多厘米的正方体家具,柜子一般是从上面打开。米柜这个词汇,也是来源于南方。可能是当初移民过程中,江南的百姓将家中放米的柜子带到了青海,之后这个词汇就流传了下来。也许正是因为青海方言与南方吴语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很多青海人看一些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会倍感亲切。《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著作中,我们经常就会看到一些和青海汉语方言相似或相同的话。如《金瓶梅》第八回中有这样一句话:“等我掐你的皮脸一下。”《金瓶梅》第十九回写道:“险不倒栽阳沟里。”“皮脸”和“阳沟”青海汉语方言中一直都在使用。皮脸就是脸的意思。被盖住的小水渠称为阴沟,没盖住的小水渠叫阳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聚居区,所以青海方言中也融入了很多少数民族语言词汇。这些词汇也被称为借词。在青海方言中,习惯把事物达到极致称为“胡都”,例如“胡都美”就是非常美,“胡都大”就是特别大,还有称全部为“一挂”。“胡都”和“一挂”都源于土族语言。青海人称有一定技能的人为把式,例如拳把式,就是会打拳的人。称头为“朵落”,“倒朵落哈了”意思就是头朝下了。这两个词汇是蒙古语的借词。“麻浪子”是“等等”的意思,源于撒拉语,如说“今年豆儿、洋芋麻浪子收成还中俩”。青海方言中还有许多藏语借词,例如“囊玛(音译)”意思为内部。“卡玛”意为标准、规范等。当然,这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含义也并不尽相同,例如说:这件衣服你穿上的卡玛没有,这里的卡玛意为合身、合适。这个人办事儿没卡玛,这里的卡玛意为规矩、把握。在青海有些民族杂居的地方或农牧交会区,还流传着“风搅雪”的表达方式。风搅雪原意为风雪交加的天气,在青海方言中则指的是青海汉语方言与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相交混使用的语言现象。上世纪60年代,我去贵德考察,在河东乡王屯和东沟乡周屯等地发现,当地老百姓说的青海汉语方言有一部分我能听懂,另一部分根本听不懂。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说话的方式就是“风搅雪”。考察那天,一个年轻人问一个老汉:“阿布阿爷阿扎去了?”意思是爷爷你去哪里了?阿布是藏语音译,意为爷爷。阿爷是汉语,也是爷爷的意思。这样的表达,不管是藏族百姓还是汉族百姓都能听明白意思。青海方言中使用借词和“风搅雪”体现了少数民族语言对青海汉语方言的影响以及各民族对彼此文化的尊重。这种表达方式也经常出现在青海“花儿”中。青海汉语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因为受到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些青海本地特有的词汇,这些词汇为青海汉语方言注入了一些新的、独有的元素。就是这些词汇只有青海人懂,其他地方的人很难理解。在我国很多地方腊八节有喝腊八粥的习俗,但在物产不丰的青海要找齐腊八粥中的八宝十分困难,于是青海人便创造了麦仁饭。麦仁就是青海方言中的原创词汇。还有用青稞面做的吃食“黑油尜儿”。中间青稞面,外包白面类似花卷的“砖包城”。用荨麻做的“背口袋”,还有用青稞面做成的“破布衫”等。镫扎皮原本是马鞍上连接镫与镫的宽皮带,发展到后来,镫扎皮成了一种宽扯面的称谓。这些都是青海老百姓智慧的结晶,也是青海汉语方言中最为独特的部分。青海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隐语,一般表达不好说或隐晦的事儿。例如,青海人说吃老虎是指接吻、吃羊头是指骗人、人言的意思是砒霜、袖子长是指有狐臭等等。还有旧时青皮行中的商业隐语,例如箭表示一、丑为二、藏为三、苏为四、炮为五……在青海这方热土上,方言不断变化、完善,还形成了一些特立独行的词汇。比如“羊肺肺”一词,这个词汇来自青海人民长期的生活经验,青海人在煮食羊肺时发现,由于羊肺中存在大量的气泡,使得羊肺很难沉入水中,总是浮在上面,于是有了“羊肺肺压不倒锅底”的说法,后来专指那些说话不着边际、空话大话张嘴就来的人,没有高原生活的基础,没有与游牧民族相互借鉴,就不会有这个词汇。还有比如“乌拉”一词,它是藏语劳役的意思。它产生于清代军队的青藏粮台建制。粮台相当于今天的兵备战,当时粮台有权利征集劳工,搬运辎重。青海汉语方言中的“乌拉”意为被使唤的工具。“我不是你的乌拉子!”表示不甘被奴役,语义中充满了反抗情绪。“我是人家的乌拉子。”有自贬的意思,希望引起对方同情。清朝灭亡后,青藏粮台建制逐渐废除, “乌拉”这个词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青海人民又发明了一个词来代替“乌拉”的意思,那就是“板镢”。板镢原指一种用于农耕的宽口锄,青海汉语方言中其意思被引申,一个被使唤的人。这些词语的创造和变化,让青海方言不仅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生生不息的活力。青海汉语方言以汉语的语法为框架,但是因为受古汉语语法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青海汉语方言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例如,将否定副词放在形容词的后面,如:这个娃娃好好不学习。青海汉语方言中还习惯将宾语放在谓语的前面。例如青海话说:“阿舅,酒喝上点,馍馍吃上点。”有学者考证,这种语法是受到少数民族语法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语法是古汉语的语法,《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沛公安在?”意思是沛公在哪里?这句话将宾语“安”放在了动词“在”的前面。在语音方面,青海人的口头发音最显著的特点是前鼻后音混同。例如“云”和“永”“龙”和“仑”等。除此之外,青海人说话还喜欢使用一些语气助词,如“呗”,好久不见,你变漂亮了呗!“撒”,你好着撒?“说”,家(他)作业没写说(他没写作业)等。青海汉语方言中还会使用许多富有特色的词。比如喜欢使用叠词,树树、车车、碗碗、刀刀、桌桌……重叠以后,如果表示小而可爱,会在后面加上“儿”字,如刀刀儿、勺勺儿等。当形成“AA儿的”时,重叠的第二个音节的音程可以适当延长,这样可以起到增强程度的作用。如,远远儿的,表示不是很远。远远——儿的,则表示距离比较远。“动词+着”或“形容词+着”也是青海汉语方言比较常见的语式。其中,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多次重复,最后的“着”可以拖长读音,以表示程度的加深。例如:再我把你想着想着想着——。家(他)把我好着好着好着——。“早”是时间副词,青海汉语方言中却喜欢将它放在主语之前,做状语。表示“现在”“就”的意思。例如:早你快点,家走掉好一会儿了。你等着,早家来俩。“脱了”在青海汉族方言中也是时间副词,表示动作开始或正在进行。例如:河里的冰消脱了,意思是河里的冰正在融化。青海汉语方言中“们”除了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外,加在其他名词之后,表示“之类”“等等”的意思。例如:羊羊们宰上、手抓们煮上、今儿亲戚们来俩。在青海汉族方言中还有许多区别于其他方言的词汇和语法,这些内容让青海汉族方言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具特色。